巴金說,“我覺得青年時狂一點不要緊,但要有自知之明,肚里有多少墨水自己要有數(shù)。”對于青春帆船剛剛啟航的大學(xué)新生而言,認(rèn)清自我既是立身行事的根基,更是逐夢前行的智慧起點。
進(jìn)入大學(xué),迎來全新的環(huán)境,身邊多了不少優(yōu)秀的同學(xué),可能會一時摸不清方向,陷入“不知該往哪里走”的迷失。正確的自我認(rèn)知,如同一張內(nèi)心地圖,能幫助同學(xué)們在新天地中不斷校準(zhǔn)人生航向。先認(rèn)清自己,擺正位置,在不斷嘗試中找到適合自己的事情,不做不切實際的幻想,才能從容不迫地走好人生道路。“人貴有自知之明”,這是一句歷經(jīng)反復(fù)檢驗而顛撲不破的哲言。
正如硬幣有兩面,認(rèn)識自己也要分兩面:既要看到自己的長處,也要看到自身的不足。面對新環(huán)境新挑戰(zhàn),倘若看不到自己的優(yōu)點,就會喪失前進(jìn)的信心;而看不到自己的短處,又會因自滿而停滯不前。人要自知,最難的是拿捏分寸——不看輕自己,也不高估自己;不給自己設(shè)限,也不自我膨脹,而是清楚地知道并不斷拓展能力的邊界。全面、正確地認(rèn)識自己,既“揚己之長,克己之短”,又“學(xué)人之長,避己之短”,才知道如何有效地提升自己和改造自己。
“不自知”與“有自知”,往往是決定一個人成敗的關(guān)鍵。《資治通鑒》記載,唐太宗以隋煬帝“恃其俊才,驕矜自用”終致亡國為鏡,發(fā)出“人苦不自知”的慨嘆;反觀唐太宗自身,因清醒認(rèn)識到“兼聽則明”的道理,虛心納諫、廣納賢才,才開創(chuàng)了貞觀盛世。這表明,無論身處何種位置,看不清自己的能力邊界,忽視自身短板,往往容易栽跟頭。治國如此,在學(xué)業(yè)上,在科研中,又何嘗不是如此?對于大學(xué)生而言,自知意味著清晰認(rèn)知自己的知識儲備、專業(yè)特長與性格特質(zhì)等。知識儲備有哪些薄弱環(huán)節(jié),自己的優(yōu)勢如何發(fā)揮出來,唯有在認(rèn)清自我后找準(zhǔn)方位,才能不陷入“別人都選的路就是對的路”的誤區(qū),進(jìn)而真正找到契合自身發(fā)展的賽道。
其實,越是博學(xué)之人,越知道宇宙之浩瀚與己身之渺小。牛頓晚年自喻為“海濱玩耍的孩童”,僅為拾得幾枚真理的貝殼而欣喜,面對真理的海洋仍心懷敬畏;諾貝爾成就斐然,卻用“無”字概括一生的重要事跡。他們的偉大,不僅在于探索世界的深度,而且在于洞察自我的清醒。事實上,越強(qiáng)大的人,反而越低調(diào)、越謙卑。正如成熟的麥穗,粒粒飽滿,卻笑意盈盈向下低頭。這與夜郎自大者的狹隘,形成云泥之別。當(dāng)代大學(xué)生身處知識爆炸的時代,更需銘記:知之愈多,愈覺所知之少。永葆謙遜與好奇,摒棄“半瓶水晃蕩”的浮躁,方能不斷完善自我、接近真理。
值得警惕的是,認(rèn)識自己不是“一切以自我為中心”。如果一個人只是圍繞“自我”打圈子,那么他的一切創(chuàng)造都不可能擺脫私有觀念的束縛,這是非常危險的。當(dāng)他的個人利益得不到滿足時,就會悲觀失望,喪失生活的信心,甚至?xí)繐p害他人利益來滿足私欲,最終走向罪惡的深淵。正如錢理群教授所提醒的,大學(xué)生不能成為“精致的利己主義者”。真正的自知,是超越狹隘自我,將個人的成長與社會的需求緊密相連,在更廣闊的坐標(biāo)系中實現(xiàn)價值。
俗話說,當(dāng)局者迷,旁觀者清。大學(xué)生涵養(yǎng)自知的智慧,既需“向內(nèi)審視”的自覺,也需“向外借力”的智慧。不妨通過“總結(jié)法”復(fù)盤得失,在反思中看清自己的進(jìn)步與不足;用“換位法”傾聽他人意見,把同學(xué)的建議、老師的批評當(dāng)作認(rèn)識自我的“鏡子”,避免不自知的局限;以“對比法”校準(zhǔn)方向,對照學(xué)生守則檢視言行,以先進(jìn)模范為標(biāo)桿尋找差距,在與角色規(guī)范、榜樣先進(jìn)、過去自我的比較中,既認(rèn)清當(dāng)下的自己,又明確未來要成為的自己。
“認(rèn)識你自己”,這句鐫刻在古希臘德爾斐神廟上的箴言,如今依然閃耀著智慧光芒。大學(xué)生正處于塑造自我、成就未來的關(guān)鍵階段,當(dāng)以自知為基,滿懷“少年負(fù)壯氣”的豪情,保持“知己所長、明己所短”的清醒,在認(rèn)清自我中錘煉本領(lǐng),在腳踏實地中追逐夢想,讓青春在精準(zhǔn)定位、矢志奮斗中綻放絢麗之花!
原載:2025年9月18日《新華日報》,版次:3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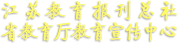
 蘇公網(wǎng)安備 32010602010084號,
蘇公網(wǎng)安備 32010602010084號,